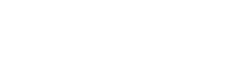浙江獐子养殖场(不吃“个别的肉”——从保护野生动物说到爱惜粮食)
近日,《检察日报》发表文章《为野生动物撑起“保护伞”》,文中认为,保护野生动物正是更好地维护生态,促进农业和粮食生产,是对“节约粮食,爱惜粮食”行动的支持。
无论什么野生动物,都与我们共享了整个地球。它们在生态系统中,占据了自己的生态位,为生态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。它们需要自己生活,自己捕食,自己逃避敌害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野生动物在道义上和我们人同是大自然的共享者,为生态系统做着自己的贡献。
从另一个角度说,保护野生动物,倡导“舌尖上的文明”,也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文化。好像我们看到一件古时的书画,感觉它们历经沧桑,见证了一个时代,独具匠心。可是很多人看到野生动物,却没有这种感觉。其实每一个物种,经历了地球万年乃至亿年的进化,这是自然的馈赠,自然的遗产,代表了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,看到野生动物,发于河洛,生于荒野,静静地不被世俗的工业社会打扰,这是一种最质朴的美。我们说一幅普通的古书画留着有必要吗?单单就经济效益而言,简直微乎其微,但是它的文化意义非凡。
中国作为全世界最早进入农耕时代的地区之一,一直有较高的文明程度,按理说,会以食用驯化后的动植物为风尚。但今天的华人世界,为什么会逆其道而行之,以吃野味为荣呢?而且作为一种需要立法来制裁的陋习,肯定其来有自。今天的“国风堂”,就和读者聊一聊吃野味的暗黑史,以及人们对于食野味的反思。

食野者鄙
翻看中国的史书,记载里除了盛世的太平年景,天灾人祸也不少,而且每次灾难还伴随着类似此次瘟疫的重大事件,老百姓往往流离失所,易子相食。那个时节,“吃什么”就成了身份的象征。
当然了,人类最初也是意识到了肉类的美味,不过作为普通百姓,连饭都吃不上,恐怕只能“望肉兴叹”,可见能吃上肉的还是少数人,不是限购,而是特供。
正因为吃肉对于普通百姓太难,以至于中国文化中的奸臣往往是肥头大耳,比如董卓。对于商纣王“酒池肉林”的评价,人们丝毫不去探究这背后的背景以及传统,这几乎成了商纣王的原罪,我们吃不上肉,你吃肉不仅可耻,还可恨!
根据文字记录推断,那时的肉食者吃的还是正经的肉。《周礼》中,记载了周天子大宴的场景。“士”被赐予一鼎或三鼎,食物配置是豚(小猪)、鱼、腊(腌肉);“大夫”对应的是五鼎,标配了羊、豕(大猪)、肤(切肉)、鱼和腊;“卿”或“诸侯”对应的是七鼎,包括牛、羊、豕、鱼、腊、肠胃(下水)、肤;“天子”才能享用九鼎,包括牛、羊、豕、鱼、腊、肠胃、肤、鲜鱼(新鲜的鱼)、鲜腊(新腌的肉)。
显然,以牛、羊、猪、鱼为代表的贵族宴席上,都是正常生产养殖的家畜。虽然当时“六畜”之外,还有“六兽”和“六禽”,但那些都不能登上正式宴席的餐桌。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野味的功能定位,最多只是中下阶层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,或是贵族阶层吃腻普通食物后调剂口味的道具。
由此也可看出,在古代中国,野味是地位较低的食物。这种饮食观,其实伴随了中原王朝千年之久。在后世对边远地区吃野味的记载中,但大多是以猎奇、甚至带着鄙夷的色彩笔墨叙述的。汉朝的《淮南子》说:“越人得蚺蛇以为上肴。”对长江以南人吃蛇的鄙视溢于言表。
到了唐宋,江南大开发已经基本完毕,江南的经济文化不输中原。这一时期,对吃野味的鄙视向南延伸到了岭南地区。唐朝的《岭表异录》说广东人吃鹦鹉、猫头鹰,简直不可思议。宋朝《岭外代答》中更说:“深广及溪峒人,不问鸟兽蛇虫,无不食之!”言语之中,都是对岭南人粗鄙的不屑。
以食用正常生产养殖的五谷杂粮和家畜为主流,在戏文里也可看到端倪。有一段河南曲子《关公辞曹》,戏里曹操是这么唱的:“曹孟德在马上一声大叫,关二弟听我说你且慢逃。在许都我待你哪点儿不好,顿顿饭包饺子又炸油条。你曹大嫂亲自下厨烧锅燎灶,大冷天只忙得热汗不消。白面馍夹腊肉你吃腻了,又给你蒸一锅马齿菜包。搬蒜臼还把蒜汁捣,萝卜丝拌香油调了一瓢。我对你一片心苍天可表,有半点孬主意我是……”
戏曲虽非正史,但却是当时百姓生活的最贴切反应,在正史难以记录的空间,发挥着它的特殊作用。当然在三国的时代,特权阶级也是会享受的,比如董卓的肚子大得惊人;比如何不食肉糜,比如袁术在血水横流的战场讨要蜜水喝。而曹操笼络关羽,也远非几顿包子肉夹馍可以解决的,就像“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”不可能一样,在吃上的想象,地方戏和小说家言体现出的,都是最高愿望的美化,好像当时的王宝强,他还没出名的时候,最大的愿望就是过年回家买个卧铺票。
可以说,社会主流以食用驯化后动植物的农耕文明,一直持续到了明末,为野味披上贵族衣裳的,据说和满清的入关有关系。
作为文明程度落后的东北渔猎民族,女真的社会发展程度是很低的,甚至比当时的蒙古还低,但满清政权一直力主学习和融合。一方面,康雍乾诸代皇帝,都努力学习汉文、起用汉吏、制定汉规。但另一方面,满清贵族又努力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,并促使汉族学习自身的文化,比如吃野味。
至今流传的“水陆八珍”,就是在乾隆朝成型,其中就有鹿筋、蛤士蟆、熊掌、鹿尾、象鼻(一说犴鼻)、驼峰、豹胎、狮乳、猕猴头等;而在上中下八珍中,也包括猩唇、驼峰、猴头、熊掌、凫脯、鹿筋、黄唇胶、豹胎,以及果子狸。这些,都是满清以吃野味为“珍”,并引领汉族学习的证据。
对比一下成书于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的《金瓶梅》和著于清代中叶的《红楼梦》,就可看出个大概。
《金瓶梅》里写:“先放了四碟菜果,然后又放了四碟案鲜:红邓邓的泰州鸭蛋,曲弯弯王瓜拌辽东金虾,香喷喷油炸的烧骨,秃肥肥干蒸的劈晒鸡。第二道,又是四碗嗄饭(即佐餐菜肴):一瓯儿滤蒸的烧鸭,一瓯儿水晶膀蹄,一瓯儿白炸猪肉,一瓯儿炮炒的腰子。落后才是里外青花白地磁盘,盛着一盘红馥馥柳蒸的糟鲥鱼,馨香美味,入口而化,骨刺皆香。西门庆将小金菊花杯斟荷花酒,陪伯爵吃”。
著于《红楼梦》里,描述贾府过年的食物有:“大鹿三十只,獐子五十只,狍子五十只,暹猪二十个,汤猪二十个,龙猪二十个,野猪二十个,家腊猪二十个,野羊二十个,青羊二十个,家汤羊二十个,家风羊二十个,鲟鳇鱼二个,各色杂鱼二百斤,活鸡、鸭、鹅各二百只,风鸡、鸭、鹅二百只,野鸡、兔子各二百对,熊掌二十对,鹿筋二十斤,海参五十斤,鹿舌五十条,牛舌五十条,蛏干二十斤……
可以看出,当时临清首富西门大官人请客的,无非是些做工考究点的正规吃食,加一两道鲥鱼的时令奢侈品;而贾府的过年食材,野味就占到了相当的比例。由此可见,满清吃野味,对汉文化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。
本文写作参考了芙蓉王:《中国野味,一场壮阳与权力的千年轮回》;魏水华:《中国野味上位史》;澎湃新闻:《柳叶刀刊发中国学者评论:新冠病毒肺炎与野味消费的关系》。
野味上位
宋以后,社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生产方式的进步,中外交流的增多带来农作物的引进,促进了人口的大发展,慢慢地野味野味走上主流餐桌,这些资料是主流较认可的说法。至于中医也成了“背锅侠”,那就有必要来特意交代一番了。
唐以前,是中国传统医学百花齐放的时代,经方派、温病派、扶阳派等等和不同的实践,百花齐放,似各种武术流派一般。但宋以后,一个独特的现象出现了——文人参与医学。范仲淹说的“不为良相,即为良医”,就很能代表这一风气。
魏水华在《中国野味上位史》里有个观点:“文人参与医学有两个可怕的后果,一是中医越来越脱离临床经验,转而寻求哲学支撑,今天仍然流行的中医理论术语,大部分都是宋中叶之后介入;二是外科的介入治疗对文人来说相对困难,而选药、煎汤则简单得多,这就奠定了后世中医重汤方、轻外科的习气。慢慢地,《五十二病方》《伤寒杂病论》这些基于临床的著作被逐渐边缘化,而一些基于哲学和汤方的著作则逐渐成为中医最重要的典籍。”
自此之后,刮骨疗伤的华佗再也没出现过,取而代之的是无数一副药方治百病的文人。
而作为汤剂的材料,中药的选材当然是越少见、越稀有,治病价值越高。一块猪肉、一条鲫鱼能治病,别说病人不信,文人中医们自己都不信。按照这一逻辑,产自深山老林里的稀有动植物,肯定对某种疾病有奇效。
在这种思维模式的主导下,明清两代,出现了大量野猪肚养胃、蛇胆清火、夜明砂(蝙蝠粪)明目的理论,至今盛行不衰。而基于中医“药食同源”的思想基础,野味也更多地被作为名贵的滋补品,送上了中国人的餐桌。
当然,还有些更离奇的。鲁迅先生在《父亲的病》里,提到了好几种奇怪的药引,比如经霜三年的甘蔗、原配蟋蟀一对、由敲破的鼓皮做的“败皮鼓丸”,鲁迅先生写“最平常的是‘蟋蟀一对’,旁注小字道:‘要原配,即本在一窠中者。’似乎昆虫也要贞节,续弦或再醮,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。”
凭心而论,鲁迅对这些具体问题批评的都是对的,点到了某些中医的痛处,当然也难免有些偏颇。后来鲁迅坦诚地说:“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,但怕也很夹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”(《坟"从胡须说到牙齿》)。由此看来,鲁迅并不是在反对中医,而是批判庸医。只是响箭过处,不小心击中了医林中的几片黄叶而已。鲁迅后来对《本草纲目》和民间医药的评价(《二心集"经验》),公允而且深刻,就足以证明这一点。
说穿了,吃野味在古代是因为食材匮乏,代表着尊卑,延伸到现代,则为不良商家的炒作和食用者的虚荣心,冒充医学养生的噱头来营销而已。
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里就总结了一大堆不能吃的“野味”,否定了民间所谓“吃啥补啥”的说法,比如:孔雀肉味咸、凉、有小毒,人食其肉者,自后服药必“不效”;熊肉,“有痼疾者不可食”。
简单科普一下中学生物:不论野味身上有啥营养,吃到肚里能被我们消化的,都只有糖类、脂肪、蛋白质。至于被吃得濒临灭绝的穿山甲,从化学和营养学角度看,它的鳞甲,其实就是角蛋白,说得再明白点——跟咱的手指甲、脚趾甲的“营养成份”是一样一样的。
过来人言
姜先生五十来岁,是名老餮,在外搜罗野味二十多年,三年前不吃了,不过对于食用野味的看法,他还是有发言权的。老姜吃过的野味数量不少,像蛇、獐子、麂子、娃娃鱼、石蛙一类是常见的,有些他还说不出口。他反思了自己不吃野味的经历。
老姜总结自己吃野味,第一原因是贪吃,在好奇心和猎奇心的驱使下,对于没吃过的东西,老姜都想吃一吃;其次是老姜接触到朋友圈子广,早些年他能遇到一些完成了原始积累的人士,那拨人有钱之后的,开始炫耀性消费,穿山甲都是一头一头地吃。
老姜最早吃野味的时候,是到店里吃现成的,因此他还感受不到残忍和不卫生。何况对于野味又是刚刚上口,吃过之后还感觉很有效呢,因此三天两头吃,还吃出花样来,像眼镜蛇和娃娃鱼,都发展出一物几吃,吃得不亦乐乎。
2003年的SARS,老姜消停了一阵,大约有七八个月吧,之后又故态重萌。不过这时节老姜开始走起了户外,本来是走户外和吃野味并举的,但是一次偶然的经历使他感触颇深,并对吃野味有了抵触。那是一次进山吃“山头黄鱼”之旅(其实是吃穿山甲,野味产业链上经常会用一些暗语避人耳目),他无意中走进了厨房,发现穿山甲的的神情就如初生的小儿,震撼至极。那天老姜的筷子虽然还是伸进了那一盆红烧肉类,却已是食不甘味。
再后来,随着户外的经历越多,老姜对野生动物的关系也发生着变化。他说每回在山里看到足蹄被夹断的黄麂子,被电网电到的小野猪,被人用刀剁下头来剥皮的蛇,会生起恻隐之心,甚至这些画面还会经常在他浮现,老姜开始下决心不吃野味了。
当然促使老姜不吃野味,还有一个原因是健康考虑。比如老姜吃眼镜蛇,很爱吞蛇胆和吃凉拌蛇皮,后来随着对野味加工了解越来越多,蛇皮上的寄生虫让老姜不寒而栗。老姜说,一样寄生虫就让人怕成这样,更不要提那些看不到的病毒了。
再一个原因,是口味的转变。老姜说,有些人觉得野味的味道很好,那是他们想象的。如果不是内行人,烧出来的大部分野味,是不好吃的。
比如麂子,肉有点酸,骨头多,很难炖软,当然做好了是挺好吃的,可是什么肉做好了不好吃呢?较起真来,还不如羊肉好吃呢。还有野猪肉,烧得不到位或者火候不到,皮糙肉厚的煮很久都咬不动。
老姜认为,多数的吃客是很好骗的,比如有一次在朋友家吃大盘鸡,主厨说用的料是老母鸡。但老姜知道,老母鸡是不可能烧出这种鲜嫩口感的,就偷偷问主厨,主厨也不隐瞒,悄悄说其实用的是养殖的白羽鸡。
从少吃到彻底不吃野味,这个过程持续了三四年。现在的老姜,就像那些戒断吸烟的老烟民反过来痛恨吸烟一样,几乎是不遗余力地反对吃野味了。老姜手机的微信里收藏了两段话,经常发出来规劝别人。
一段是梭罗《瓦尔登湖》的片段:“第二年,有时我捕鱼吃,有一次我还杀了一条蹂躏我的蚕豆田的土拨鼠——它颇像鞑靼人所说的在执行它的灵魂转世——我吃了它,一半也是试验性质;虽然有股近乎麝香的香味,它还是暂时给了我一番享受,不过我知道长期享受这口福是没有好处的,即使你请村中名厨给你烹调土拨鼠也不行。”
另一段是周作人先生说的:“有些飞走的小动物,不必搜求来吃。既有普通的鸡豚也就可以够了……无须太过馋痨,一心想吃个别的肉。”
看过此文的,还浏览了以下内容
相关推荐
热门排行
- 1柯尔鸭是什么鸭子?2021年养柯尔鸭赚钱吗?
- 2养殖业什么最赚钱农村项目,这6个养殖项目,想农村创业的可以试试
- 3马的繁殖技术
- 4野鸡晚上在哪里?几个捕捉野鸡的小技巧_库百科山鸡养殖
- 5竹鼠种类图片大全_库百科竹鼠养殖
- 6梅花鹿的发情鉴定与配种方法_库百科梅花鹿养殖
- 7水貂皮和貂皮的区别_库百科水貂知识_库百科水貂
- 8鸭子要下蛋的前期反应 新鸭下蛋前的征兆
- 9地锦草的功效与作用:地锦草治糖尿病是真的吗?
- 10常见蜗牛种类大全 蜗牛的种类大概有多少
- 11野鸭子是国家保护动物吗_库百科养鸭
- 12水貂好还是貂好_库百科水貂资讯_库百科水貂
- 132021年最新20张大合集来了,看有没有你认识的?
- 14观赏鱼烂尾烂鳍烂鳞用什么药?
- 1510万元刚需,蓝电E5荣耀版与启源Q05,谁更贴近你的出行需求?